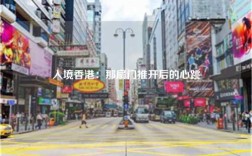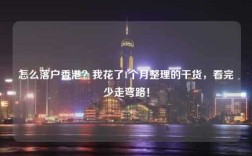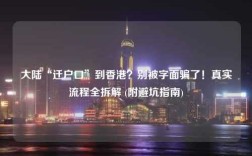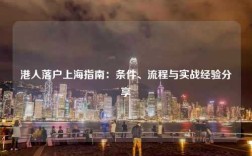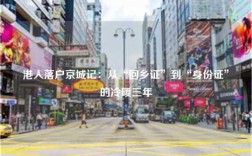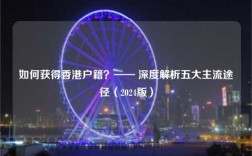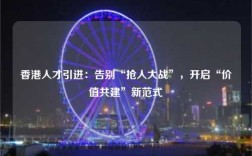香港身份:一场没有锣鼓的“过河”
湾仔入境事务大楼的冷气,是那种刻骨的冷。窗外是七月香港特有的黏腻暴雨,雨幕把维港的天际线冲刷得模糊不清。我攥着那张薄薄的“申请核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”表格,指关节泛白。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方格与选项,像一条条无形的边界,横亘在我与一个尚未清晰定义的“新身份”之间。

第一关:纸面“围城”
“永居”申请,绝非填张表格便万事大吉。七年的“通常居住”是硬门槛——签证类型、离港天数记录、税单、强积金供款凭证、水电煤气账单……材料清单长得令人窒息。每一份文件都是时光的切片,需要严丝合缝地拼接,证明你确实“扎根”于此。
最棘手的是那张“七年居住证明”。某年频繁出差,离港天数险些踩线。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会议邀请函、差旅票据,甚至厚着脸皮请前雇主出具证明信。当入境处职员最终在文件上敲下确认章时,后背竟已沁出薄汗。纸面围城,步步惊心,每一步都在无声拷问着:这些年,你究竟“在”哪里?
“粤语关”:舌尖上的身份烙印
语言,是无声的试金石。自认日常交流无碍,直到那次“基本法及香港历史”面试。考官是位和蔼的老先生,一口地道粤语,语速平缓。当被问及“新界原居民权益”时,一个关键粤语词汇卡在喉间,情急之下竟用普通话替代。老先生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捕捉的停顿,随即用粤语温和追问细节。那一刻,舌尖的笨拙暴露了“新来者”的底色,尴尬如芒在背。
后来才懂,流利的粤语不仅是工具,更是融入本地肌理的无声密码。它像一把无形的钥匙,能开启街坊茶餐厅阿姐的善意笑容,也能在职场茶水间的闲聊中悄然弥合缝隙。语言关,考的是舌头,更考一颗真正愿意“埋堆”的心。
身份“过河”:剪断脐带那一刻
获批通知寄达时,竟无预想中的狂喜。真正刻骨铭心的时刻,是去中旅社注销内地户口、领取“回乡证”那天。交出那本熟悉的紫红色小册子,接过深蓝色塑料封皮的回乡证。工作人员熟练地剪下旧证件一角作废,剪刀“咔嚓”一声轻响,像剪断了一根无形的脐带。
走出大门,阳光刺眼。手握新证件,身份却仿佛悬在半空——它不再纯粹是故乡的印记,也尚未成为此岸的完全体。一个朋友说得好:“换了证件,不过换了张船票。最难的是,心里那条河该怎么过。” 那一刻才真正明白,真正的“过河”,是承认自己将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“之间”状态——带着故土的印记,努力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心跳。
如今,我依然习惯在茶餐厅点一杯丝袜奶茶,也偶尔怀念故乡街角那碗滚烫的豆汁。香港身份,从来不是一场锣鼓喧天的“更名换姓”,更像一场静水深流的蜕变。
那把象征“永居”的伞骨是香港,撑开的伞面却仍是中国底色。伞下的人,正学着在两种风雨中从容行走,将“根”深深扎进这流动的土壤——这身份的真正分量,不在于一纸文书,而在于每一次开口、每一次驻足、每一次在心底默默认领这片土地的晨昏冷暖。
伞下的路,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