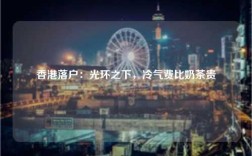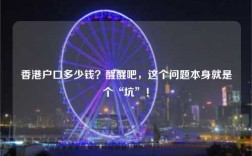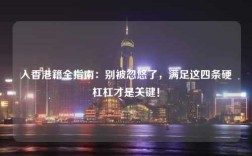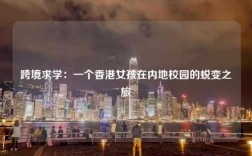入港籍:一纸身份后的千钧重量
那天下午,我捏着那张薄薄却沉甸的“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申请表”,指尖能清晰感受到纸张边缘微微的锐利。窗外香港的摩天楼群浸在一种粘稠的午后暑热里,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白光。空调的凉气吹在颈后,却带不走心头那点悬着的重量。我握着笔,几乎能听见笔尖划过表格时发出的沙沙声,每一个空格都像是一道小小的门槛,横亘在我与“香港人”这个称谓之间。

第一步:纸页间的跋涉
那几张表格,远非填上姓名地址那般轻巧。它要求你将自己过往人生里所有重要的时间节点、空间轨迹都压缩进冰冷的方框之中。每一栏都像一道小小的审判,逼着你回溯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到了“申请成为香港人”的这个坐标点上。在“在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”的证明要求前,我翻箱倒柜,把七年来每一份租房合同、水电煤单、银行月结单都摊开在桌上。那些纸张无声地堆叠,仿佛一座由时间垒砌的沉默小山——原来七年光阴的具象,不过就是这叠越来越厚、边角磨损的文件。
最难啃的骨头是那张“税单”。某段短暂工作的雇主早已杳无音讯,那张证明收入与纳税的纸片仿佛沉入了海底。几番周折,托人辗转联系,近乎恳求,才终于拿到一份字迹模糊的复印件。当那份带着陈旧打印机油墨味的文件最终被入境处职员认可收下时,我靠在走廊冰凉的墙壁上,长长吐出一口气,仿佛卸下了背上无形的巨石。
第二步:语言的温度与刻度
“基本法测试”与“中文(粤语或普通话)口语能力评估”,是横在纸面程序之外的另一重山峦。基本法条文密密麻麻,字字严谨,只能靠反复诵读硬生生刻进记忆深处。考试当日的灯光白得晃眼,试题在眼前展开时,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在安静的考场里回响。
真正的考验是粤语面试。考官是位面容和善但眼神锐利的长者,一句“点解你决定成为香港永久居民?”(为何你决定成为香港永久居民?)抛过来,带着家常般的随意。我手心微微出汗,努力调动着那些练习了千百次的词语和语调,试图让发音再清晰一点,再自然一点,仿佛舌尖笨拙吐出的每个音节都在替我剖白内心最真实的理由。走出考场时,阳光刺眼,后背衬衫已被汗浸湿了一片。
第三步:仪式,与身份的加冕
收到批准信的那一刻,没有预想中的狂喜,只有一种尘埃落定般的踏实感。邮件里那个“批准”的印章,像一枚小小的烙铁,终于盖在了心头悬而未决的位置。
宣誓仪式安排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一个庄重而不失明亮的礼堂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期待与肃穆的气息。当被念到名字,我与其他几十位“准新香港人”一同起立。眼前是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。领誓员的声音清晰沉稳:“本人谨此宣誓:本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约束,尽忠职守,遵守法律,廉洁奉公,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…” 我逐字逐句跟读,声音不高,却异常清晰地回响在耳畔和自己心中。当念出“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”这几个字时,舌尖仿佛触碰到了某种沉甸甸的实质。
仪式结束,走出那栋大楼,维多利亚港的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阳光依然炽烈,林立的高楼反射着恒久的光芒。手中那张新换领的、印有紫荆花图案的智能身份证,边缘光滑,不再锐利,却蕴含着比之前那份申请表更沉实的分量。
入籍并非终点,而是起点。
这重量,源于它不仅是法律身份的确立,更是一份无声的契约。契约的一方,是这片土地赋予的归属与权利;另一方,则是我们需以行动去践行的承诺——理解她的历史脉络,融入她的市井烟火,遵守她的法律规则,参与她的未来建设。
成为“香港人”,从此你不再仅仅是这繁华都市的过客或旁观者。她的兴衰冷暖,她的霓虹璀璨与街头巷尾的烟火人间,都将与你息息相关,血脉相连。这份重量,是责任,亦是归属,从此沉甸甸地,落在了肩头,也刻进了生命里。每一步,都需走得踏实;每一次呼吸,都带着港湾的气息。